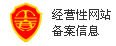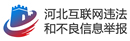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追忆难忘的烽火岁月,戏曲界宣传抗战的代表人物高庆奎,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炮响,积极宣传抗战,他始终用京剧作为武器,把民族大义唱进百姓心里。
京剧大师高庆奎是高派老生艺术创始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高庆奎原籍山西榆次,生于北京,20世纪30年代与余叔岩、马连良被誉为老生“三大贤”,以《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碑》“三斩一碰”,以及高派经典剧目《逍遥津》著称。高庆奎将高派艺术的激昂慷慨之风格与抗战主题深度融合,其唱腔鹤唳九霄,情感饱满,极具感染力,使观众在审美中接受爱国教育,在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以艺抗战”的鲜明印记。

高庆奎《赠绨袍》

高庆奎《史可法》
借古喻今:激发民族气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高庆奎以艺术家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积极创作宣扬爱国思想、抗日救亡的京剧剧目。这一时期,高庆奎以其忧国思想编演了很多爱国新戏,通过舞台塑造出一系列的爱国仁人志士,激发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和爱国情怀。高庆奎与清逸居士(爱新觉罗·溥绪)、郝寿臣等合作,形成了“编演一体”的爱国创作群体。
其中,《史可法》讲述的是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死守扬州、城破殉国的故事。1932年10月,高庆奎在日军侵华、华北危急的背景下排演京剧《史可法》,通过史可法“被俘骂贼、不屈就义”的壮烈形象,唤醒民众对亡国之痛的共鸣,借古喻今,激励民众抗战意志。高庆奎在剧中饰演史可法,塑造出“面对强敌,竟有压倒之势”的英雄形象。剧中史可法与清军统帅多铎(郝寿臣饰)的交锋,将侵略者的嚣张与英雄的凛然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史可法》演出十分轰动,在北京、天津等地引发强烈反响。高庆奎在剧中饱含激情的一段台词:“方今强敌当前,诸将宜同心协力,化除成见,团结一致,方能救亡图存。”引起观众共鸣,每次演出都报以雷鸣般掌声,而这句台词成为人知的一句抗日口号,在北京街头时常能见到贴出这句口号标语。
有观众曾撰文评论说:“高之此戏扮相清澭洧灭,神色大方老练,能状出史阁部一代纯臣之意境。大段唱工之凄凉哀婉,如闻杜鹃啼血,真能有‘以身入戏’之化境功夫,迄今回忆思之,耳目中尚有历历清楚之慨也,处兹民族意识荡然的现在,政府应当倾力提倡此剧。”高庆奎通过《史可法》的演出,展现了民众的勇气与决心,传递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一篇剧评这样评论:“其剧情可使人民增进爱国之思想,救国之观念,最宜时下演之。庆奎饰史可法,其唱作念打。无一不精。如将场训兵之口白,清楚流利,动听之至。且能将忠臣救国,训兵御辱之形态刻画尽致,是为将士之楷模。及清兵入城,对敌之起打,紧凑稳健,火炽异常。兵败以身殉国一段唱功,繁难已极。行腔使调,忽高忽低,顿挫婉转,殊是悦耳。加以天赋高亢之嗓音,犹有锦上添花之妙,诚佳剧也。”
《史可法》将艺术创新与流派传承相结合,以高派老生的高亢唱腔和激情表演,将史可法的悲愤与壮烈刻画得入木三分。剧中“修书”“骂贼”等唱段,既保留了京剧的程式美,又融入了现实主义的情感张力。高庆奎把老生唱腔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穿云裂石,如闻金石之声,观众听到的不仅是“唱”,更是人物胸中那口“天地有正气”的浩然长歌。《史可法》不仅是京剧艺术的创新之作,更是抗战时期“舞台抗战”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历史叙事重构民族记忆,以艺术之力参与现实抗争,成为戏曲史上“国剧救亡”的典范。
高庆奎的《史可法》突破禁忌,承担政治风险,他的演出面临艺术上的挑战,在塑造史可法的英雄形象时需突破传统程式,还要承担政治压力。当时日伪势力对爱国剧目严加审查,而高庆奎坚持排演《史可法》等“抗敌戏”,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体现了艺术家的民族担当。演出在北京、天津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被视作借古喻今的抗日号角。然而,这出戏也屡遭当局刁难,一度被禁演。
呈现精品:激励民族志气
《豫让桥》是高庆奎代表作之一。高庆奎与剧作家清逸居士创编了历史剧《豫让桥》,1932年4月在北京华乐戏院首演。《豫让桥》讲述战国时豫让为智伯复仇,漆身吞炭、变形变声以接近仇人赵襄子,最终刀斫仇人衣袍后自刎而死的悲壮故事。高庆奎在九一八事变后排演此剧,深入刻画豫让坚忍不屈、为复仇不惜自残的苦痛决心,演出十分感人,高庆奎塑造了一位刺客舍身报国的形象。
1932年4月22日,北平版《全民报》在头版登载大篇幅介绍高庆奎成功演出《豫让桥》报道:“《豫让桥》的剧情,是帝国主义侵略失败的先声,是民气澎湃保国卫生的镜鉴……《豫让桥》的结构,是志士舍生、誓报国仇的血痕,是英雄爱国奋斗到底的悲泪。《豫让桥》的表演,是民族精神一致御辱的成功,是烈士死节万载名扬的奇迹。”正如报道所述,《豫让桥》一剧不但情节是烈士事迹中的奇迹,从艺术上来说,也是京剧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时,高庆奎开创了京剧剧目中,同一演员饰演同一角色,并由“生”“净”应工的先河。高庆奎在《豫让桥》中,先是由老生应工豫让,等到豫让漆面吞炭之后,他改饰花脸,用自己擅长的铜锤花脸腔调饰演豫让。这样的处理方法,与剧情完全贴切,将豫让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
1934年4月27日,在北京华乐园,高庆奎与演员李洪春、李春恒、李慧琴、慈瑞泉等合作推出《杨椒山》即《杨椒山弹劾严嵩》。这部戏是高庆奎编演的新编历史剧之一,讲述了明代忠臣杨椒山(即杨继盛)冒死弹劾奸臣严嵩的壮烈故事,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台上唱到激愤处,台下观众反应强烈。正因为此剧触及时弊、鼓动抗战,演出遭到当局干扰,被迫停演,后来很少再能公演。著名演员殷野十分佩服高庆奎上演《杨椒山》的勇气,他赞誉:“华北风云日急,日寇虎视眈眈,正是国难当头多事之秋。令尊高庆奎先生排演了《杨椒山》,许多有识之士都誉为这是有非凡胆识的。”
高庆奎通过创作演出具有爱国思想的剧目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成为戏曲界宣扬抗敌救亡思想的代表人物。
参与义演:展现家国情怀
抗战期间,高庆奎以实际行动投身义演,为前线将士和难童募捐,体现了一位京剧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义演活动当时受到高度评价,成为京剧史上兼具艺术高度与社会担当的典范。
抗战初期,高庆奎随梅兰芳、余叔岩等北上南下,曾在武汉“汉口大舞台”等地参加义演,鼓舞军民士气宣传抗战。
1933年,高庆奎与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合作演出《煤山恨》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煤山恨》以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自缢煤山(今景山)的历史为蓝本,但该剧并非单纯的历史复现,而是通过“亡国悲剧”隐喻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他们以“双头牌”合作,高庆奎(老生)饰演崇祯帝时需表现亡国之君的绝望与不甘。他在剧中“撞钟鸣冤”一折的“反二黄”唱段,因情绪过于投入曾当场咳血,被报界形容为“字字血泪”。梅兰芳饰演崇祯皇后周氏(或虚构角色),以青衣的端庄反衬末路王朝的凄怆,此次合作被视为“戏曲救亡”的实践。天蟾舞台罕见地并列两人姓名于海报,打破“旦角挂头牌”或“老生压阵”的惯例,实则通过对等合作强化“国难当头,人人有责”的象征意义。演出期间,剧场外有青年散发“勿忘煤山”传单,将戏剧与抗日宣传联动,连续10场,场场爆满。《申报》评论称“观者无不感泣”,但租界工部局以“煽动民众”为由要求删减“杀贼”台词,引发剧界抗议。此后,高庆奎将《煤山恨》改为《明末遗恨》。
1932年,高庆奎在北京与荀慧生等合作义演《翠屏山》等剧目,为抗日前线受伤将士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这场义演不仅体现了艺术家的民族气节,也成为京剧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1月,榆关(今山海关)战事爆发,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榆关抗战打响。高庆奎迅速参与到支援榆关抗战的义演中。1933年2月1日,高庆奎举行了一场义务戏,这次义务演出是为募捐“榆关战事”前方将士举行的。当时,北京新年刚过,天气转暖,观众上座率高,剧院营业好。其他剧院都在忙着营业性演出,而高庆奎放弃了营业演出,义务戏演出选在上座率好的时候,演出的剧目专门选择了惊醒国人的新戏《史可法》,不但能募捐到更多的款项,还能激发更多观众的爱国士气。
1933年3月25日,高庆奎与郝寿臣等人在北京华乐戏院参与了一场支援长城抗战的义务戏演出,所得票款全部用于为前线抗日军队购买飞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场演出是当年京剧界响应“为长城抗战捐献飞机”号召的重要义举之一,体现了梨园行在国家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高庆奎的这些义演,不仅是艺术行为,更是爱国行动,在当时起到了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高伟强)